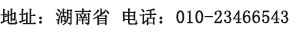什么是疾病?在人们的认知中,疾病并非是一个美好的词汇。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曾经就如何研究社会学的对象——社会事实,从分类学的角度将其划分为两类:正常现象与病态现象,正常现象为应该是什么就表现为什么的事实,病态现象为应该是什么却未表现为什么的事实。划分的依据有三条原则:普遍性原则、社会种原则、阶段性原则。其中普遍性原则即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正常现象是具有普遍形态的社会事实,并以机体的健康与疾病状态作类比。而对很多美国人来说,“疾病就是身体出了毛病,其意义不外乎定义它的一套病理机制”[1]34,并且疾病(disease)与疾痛(illness)不同,疾病是“医生根据病理理论解释和重组疾痛时提出或发明的”,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们透过各自特定的专业理论滤光镜,从患者的疾痛经验中看到的是疾病。也就是说,“患者及其家人抱怨的疾痛问题,在医生的头脑中重组简化成狭隘的科技议题,即转化为疾病问题”[2]。
如何看待疾病?从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视角看有以下几个分析维度。首先从批判主义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从疾病与权力关系入手,认为生病、衰老或者躯体失能的人因为无法对商品做出贡献而被社会边缘化,而这些弱势人群又由于处于弱势而无法享受良好的医疗条件。政治经济学批判医学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剥夺了人们控制自身健康的自主性。功能主义将疾病看作社会的离轨行为,认为得病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符合社会期望和规范,医学被看作是控制疾病破坏性、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社会建构论则认为,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常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被生产出来,主张应该从文化和社会层面对疾病进行探究。相对于医学社会学,勒普顿(DeborahLupton)认为医学人类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强调疾病的社会文化属性;其二,医学人类学所秉持的立场是一种“政治中立的微观分析”,即在勒普顿的观点中,医学人类学很少采用批判主义视角;第三,
本文即在医学人类学的疾痛叙事与医学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视角下,对在中医院整形一科就诊的先天性唇腭裂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参与观察,来描绘先天性唇腭裂患者的生活世界,展现其疾痛体验,对如何看待、对待这个病患群体进行反思,以期减轻病患的病痛。
2疾痛叙事:病患的“生活世界”作为国内唯一的一所三级医院,中医院整形一科(以下简称“整形一科”)每年暑假人头攒动,住院床位一号难求,“唇腭裂中心”的候诊走廊里站满了少男少女以及前来陪同的家长,医院外全副武装的不自然、拘谨的形态,唇腭裂患者与其家属在满是相同面貌特征的待诊区无疑是轻松的。
案例1:来自山东的刘××,女,15岁,患有先天性隐性唇裂,腭部完整,说话口齿清楚,中考结束后由全家陪同来到北京就医,5医院接受过手术治疗,是家族中首例先天性唇腭裂患者。笔者在候诊区对刘母进行了一次访谈。
“其实这次来只是听说这里看这个病不孬,我闺女之前一直在山东省内找专家看,都说她这个症状不明显,手术后也会留疤,所以都不建议做。但是咋能不看不试呢,有这道‘疤’总归是不好看的。但我觉得这次来这儿我有信心了,你看看这几个小娃娃,年龄都是四、五岁,已经做过两三次手术了,你看效果多好啊,肯定还是要做手术的,做要比不做强啊,再说别人的父母这么不辞辛苦,我们也能!”而在与患者本人刘××进行交流时,她则全程表现得腼腆而又轻松。“爸妈说要来这儿看就来了,来这儿我也没有之前想的那种尴尬。因为你看啊,这儿都是跟我一样的……姐姐,刚有个男生走过去看我,我也看他了,谁怕谁?都一样嘛!”
在初次就诊完毕后,刘××一家走出来的表情是带着些许兴奋的。“我就说能做(手术),这个大夫一看就和之前的不一样,他说能治!不过,他咋说了这么多毛病(表征)呢,他刚说两边鼻孔不一样,嘴也歪……之前咱都没看出来,不过大夫说了可以做(手术),做完效果肯定比现在要好,之前的大夫可没有这样说的!”刘父自始至终表现得很沉默,只在刘母表达完后默默安排排队入院期间的行程。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较于刘××父母的兴奋,刘××就诊后情绪低落许多。“大夫是挺好的,但我坐下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嘴我看着就不舒服’,我还不舒服呢!本来以为这儿跟外面不一样呢……我讨厌分班,因为每次分班就会有新同学,总会被问‘你的嘴怎么了?’我都说是小时候磕到后留的疤,这次高中开学肯定还是会被问。”说这些话的时候刘××表现得非常平静,“但是,我也没想到原来它不光是一道疤,鼻子嘴巴都还真有问题。”言谈中不难看出,刘××是个性格开朗的小女孩,大笑时虽然会用手捂住嘴巴,但仍然遮不住由衷的笑意。
谈及日常生活,刘母显然比之前沉重些许:“我女儿很听话的,就是性格有点急,我跟她爸是一直都要给她看这个病的,主要是这个(容貌)对女孩儿是很重要的。我们家平时都很少主动去聊她这个,只有一次学校的重要分班考试,老师发英语卷子时候到她那不知道为什么试卷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她上面有听力别人的都没有,考完成绩出来分数很低,影响了分班,当天晚上我上茅房(厕所)的时候发现她自己在被子里哭,我问她怎么了,她就说了一句‘为什么总是我?为什么我就和别人不一样!’之后就大声哭起来,我当时立马也掉泪了,只能安慰她,她爸心里也不好受。那以后,我知道,其实她也挺在意的。”
案例2:李××,男,5岁,山西人,先天性唇腭裂患者,截至年7月已在整形一科进行过四次手术。不同于案例1的山东女孩,李××并没有过多的对自己疾病的表达,更多的记录来源于他的父母、祖父母。
“我们是孩子医院里找专家看了,专家给我们推荐到这里来的。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孩子才八个月大,就那么一点点我就看着他被抱进手术室了,那时候还吃着奶呢,医生就用塑料胶布把整个嘴唇掀起来贴住、固定好,这样能不耽误孩子吃奶。第一次做完医生说效果是不错的,一年以后来复查说只有唇线那还有点疙瘩,于是做了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其实不太成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然后把嘴巴重新切开又做了第三次,还是与第一次相同的问题,这不又有了第四次,具体怎么着医生说的那些我也听不太懂。”患者的父亲边喂水边闲聊,说话间患者的母亲抱着十个月的二胎(女儿)走进来。患者的爷爷在病房的电视里给孙子调台找动画片,在患者的父母离开病房后患者的奶奶加入了访谈。“别说我孙子了,医院呆着都觉得比外面轻松,大家都一样啊,你说是不是!医院里还能蹦蹦跳跳的,那天还小声跟我说,‘奶奶,他还没有我好看!’不像在家里,话都很少,尤其是有了老二以后,他爸妈非要要二胎,我还能不明白那意思吗!都是我儿媳妇的主意,她想再生一个证明她没问题。”
李××的小姑姑与我谈的更具体些。“他一出生,家里的氛围就不是很好,亲戚朋友走动看望都会注意到,有些会直接找我嫂子问,有些是相互私下交流,所以那一阵我爸妈的身体也不太好,睡不好觉,本来添丁在我们山西也是个大喜事,但我明显看得出我爸妈不知道喜还是忧的矛盾感。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这个是多大的事,直到有一次,还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一个要好的同学来家里找我,看到我侄子,问我‘哎,你侄子是兔唇啊?’那是我第一次直接感受到这件事的存在,当时我非常愤怒,很严肃地跟我同学说请他不要这样讲,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种愤怒的感觉,虽然我也说不太清楚这种感觉怎么来的。后来,李××大一点,我就问他,你这里痛不痛啊?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他就会大声说不会。他上了幼儿园以后,我也问的少了。”
李××由于年龄小,并没有对自己病情的主观叙述,更多时候是在家人与医生的指令中听从、顺从。
3先天性唇腭裂疾病的“意义系统”3.1被建构的双重隐喻
在整形一科的田野调查期间,笔者时常会对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求医者感到惊讶,也由此引发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如果这道“疤”不是在脸上呢,还会引发整形一科一号难求的“火爆”场面吗?的确,这与面孔的独特地位有直接关联,它对我们判断身体的美感与身体的损伤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现代哲学与现代科学揭示出笛卡尔哲学中心灵与身体分裂的观点,这种观点影响了礼仪、时髦、性方面的评价以及美感的方方面面——几乎涉及我们有关得体的所有观念,这种分裂是欧洲文化的一种主要的肖像学传统的要点。我们对人及其尊严的看法,依赖于这种脸部与身体的分裂,依赖于脸部是否免于或自我免于身体所受到的遭遇。并非脸部的每一种改变都被认为是可恶的或者可耻的,最可怕的改变是那些带有动物特征的变化,如麻风病的“狮脸”、先天性唇腭裂的“兔唇”,在疾病被赋予的某些道德判断下,潜藏着有关美与丑、洁与不洁、熟悉与陌生或怪异的审美判断,更准确地说,关于美与丑、洁与不洁、熟悉与陌生或怪异的判断,其形成要早于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发生分裂并最终走向似乎对立的时刻。
其次,就感官来说,面孔的“疤痕”显得不详、衰弱、紊乱、迷失。如同案例1所展现的那般,患者刘××在面对生活的无常时,更容易将其归咎于“为什么总是我”的宿命论,更容易将生活中的不顺与自身的先天性疾病建立联系,加重对“兔唇”的憎恶、自我贬损,认为是惩罚与灾祸。我们通常会把作为疾病症状的表面征兆看作是疾痛的首要意义。除病患本身外,受到先天性疾病困扰的还有患者的父母。“不会做活(生孩子)”,“老母鸡下了个畸形蛋,你敢吃吗?”等等类似的情况同时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父母身上,更有甚者,在孩子出生后,父亲选择将母子遗弃。症状通常直接、实在、明确地意味着身体的病残或是问题,很容易被认为是不言而明的,然而这种在特定的文化中却有着约定俗成的共识。不同社会群体中,对生命这种不证自明的存在也常常存在意义上的分歧。症状的意义在特定地域的文化系统中往往赋予标准化“真理”的意涵。
亚里士多德曾经就“隐喻”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隐喻,以他物之名取代此物,是现象取代了本质的一种解读。疾病本身并非隐喻,反对疾病的文化隐喻,是反阐释,就是以多元化的感受对付“唯一的阐释”,以文化民主制对付文化等级制。因为,追溯疾病的隐喻会发现它是经济的隐喻,是西方社会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为了争夺文化领导权,维持话语权,从道德和美学上贬低其他阶级的等级制陈见,冠以普世主义的面目出现,而使得没有普罗大众认为是正常的惯习而加以接受,使得疾病也具有了阶级性。在面对先天性唇腭裂患者时,“兔子”、“兔唇”何尝不是多数面孔形态的人对付异己分子的修辞学工具?由此,案例2中李××姑姑的愤怒可以被解释,是因为“兔唇”这一带有动物特征的形容将小患者划为异类,亲属宁可接受的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疾病,而不是这种带有隐喻的污名。
3.2被建构的身体观
以身体为载体的“疾病”与“健康”的问题是学术界较为
身体同时也是结构的宏观层面与个人的微观层面交织构造的产物。对于身体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维护“面子”。戈夫曼认为“面子”实际上是一种外在的“自我形象”,我们都有管理和维持自我形象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是影响我们日常交往行为的主要心理因素。自我形象源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互动双方会透露出彼此的外表、阶层、关系等信息,并借由社会仪式化的过程将这些信息标准化后传达给对方。他人如何看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如何做面子给人看。因此,互动双方会以扮戏的方式有意识地控制身体的言行、举止、仪表等,向他人展示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借以提升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这就是人们通过“印象管理”展现自己行动的一致性,同时也显示出了我们在“人性化自我”与“社会化自我”之间的差异。笔者于年7月~8月的就医高峰阶段,在整形一科的田野调查期间发现,0岁~18岁的男童患者与相同年龄段的女童患者比例为1∶2.8,女童就医率远远高于男童,就案例中所呈现的而言,女童家属的就医动力很大一部原因是“毕竟是女孩,不好看”,“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首先就得长得好”这句话背后指涉着当今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建构,女性仍然被看作是依靠靓丽外表,且依附于男性力量的角色地位,这种社会文化形塑下的身体观严重影响着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实践。
3.3被交换的意义系统
当代社会有其自有的象征系统,构成了医学的中立属性。医生所穿的白大褂就是效率和卫生强有力的象征,而医院里哔哔作响的医疗设备则显示了其技术之高新。与此同时,一些隐喻和意象也被用来描述某些疾病,理解和体验身体、不健康和疾病的方式都是社会文化意义系统的必然产物,很多意义系统都将产生交换。医生经常发现,患者会把自己有关疾病和身体的观念与概念从自己的生活世界带入到医疗情境中,而这些想法与医学上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疾病是“医生根据病理理论解释和重组疾痛时提出或发明的”,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们透过各自特定的专业理论滤光镜,从患者的疾痛经验中看到的是疾病。医生和患者将两种意义系统拼凑到一起,而不是将自身置于患者的生活世界进行观望,甚至通过他们的努力将医学知识传递给病患,并帮助病患将这些知识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世界中去,进而改善他们的生活世界。
案例2中的母亲所背负的“污名化”枷锁,案例1中小患者的“宿命论”思想,都可以通过医生的专业话语系统给予松绑,而医生的“看着不舒服”类似的话更应该被杜绝。通过以上两个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患者的求医行为皆非其自身的主动选择,之于他们而言,被认定为患有疾病的依据也并非自身生理机体的疼痛,而是来自于旁观者的语言、眼神等肢体表现以及父母家族的“感愧”。他们察觉自身不适的方式来源于“少数即被认定为异类”的分类逻辑与大众媒体、解剖学意义上的感官“对称美”,接受手术意味着对自身偏离多数事实的修正,是对父母亲愧疚心理的听从和满足,只能在此过程中的一次次“修正术”反复提醒着先天性唇腭裂患者自身的不同。全球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疤痕问题的药物,也就是说,患者们在接受一次次无法修正的修正术。
4总结与反思《火星上的人类学家》向我们展示了大众认知中“病患”们的正常的、美好的社会生活,病患自身对于疾病的认知与调整如何达到和谐的状态[5]。疾痛的隐喻,不只是生活世界的模糊映像,其意义空间中还包含着地方性文化的深层内涵。如果说,生活世界可以提供理解病痛的宏观背景的话,那么地方性文化就是透射病痛的微观情境。罗伯特又用“受文化限定的综合征”的概念表达了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疾病研究,即“有些观察者观察到一些看来很奇怪的行为,它们有很多古怪的特征,又似乎与当地的文化情境关系密切”[1]。
身体是社会的身体,疾病是文化的建构。苏珊·桑塔格曾有言,“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4]65。不管是医生、病患、亲属都应该对这一点有所理解,抛开解剖学的人体机械论,摘下社会文化形塑的有色眼镜,才能够真正达到减轻患者痛苦的目标。疾病并非隐喻,看待先天性唇腭裂患者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自身对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警惕、抵制、消除隐喻性的思考。
参考文献可上下滑动查看[1]汉.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M].禾木,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克莱曼.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M].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4.
[3]卢普顿.医学的文化研究:疾病与身体[M].苏静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8.
[4]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5]萨克斯.火星上的人类学家[M].赵海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67,82,91-.
原文标题:伦理与疗愈:先天性唇腭裂患者的疾痛叙事,发表于《医学与哲学》杂志年第41卷,第6期,57-60页。
↓↓↓点击"阅读原文"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