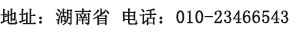袁瑞至今记得她负责过的一个病人:一个5岁多的小女孩,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治疗期间,袁瑞一直陪在她身边。因为一直跟着父母在外打工,长年住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女孩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能有一个安稳的家,有一个大大的电视。接受心脏手术后,女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在监护病房里躺了16天。袁瑞常常去看她,还拿着父母的录音给她听:「等你好起来,我们就回家,给你买大电视,买漂亮衣服。」仪器的滴滴声里,浑身插满管子、昏迷中的女孩突然流下了眼泪。图片来源:站酷海洛创意可是,她没有等到大大的电视,也没能走出病房。后来,袁瑞反复回想起这件事,几次想要动笔记录,却又因太过遗憾,在写了一半时停下。袁瑞是一名医务社工。患者:安抚与陪伴医务社工,也就是医务社会工作者。和医生的职责不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患者和家属解决疾病引起的各种心理和关系问题,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和冲突,促进患者的治疗和康复。孟燃是袁瑞的师妹,公益项目「向日葵儿童」的医务社工,在医院做儿童肿瘤方向的社工工作。他们会用游戏或者绘本的方式告诉孩子,医院,将会面对哪些治疗,可能有什么样的感受——当孩子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一个预期的时候,才能够减轻内心的焦虑和恐惧。医疗游戏中,小朋友给孟燃打针。他说:「手已经打不进去针了,需要打头,不然病不会好的。」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有的孩子害怕手术,他们就把手术比作一次探险,清楚地告诉孩子们需要准备什么,会面对什么、经历什么,甚至细致到手术室里酒精的味道、仪器发出的细小的声音。有的孩子害怕穿刺,害怕到穿刺前一天一句话都不说。他们耐心引导,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疼痛是1到分,你会给自己的疼痛打几分?哭也没有关系,想哭的时候可以哭出来。」穿刺前的干预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医院,医务社工总会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分离。如果说情绪上的问题还可以干预,可当真正到了病情恶化的时候,一切努力都显得无济于事。袁瑞和那位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孩相处了将近两个月,看着她从封闭、内向一点点变得开朗、阳光。手术前,所有人都知道风险很大。她带着女孩读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虽然听不太懂,小朋友还是很认真地跟着读,边读边笑。妈妈就坐在旁边,心如刀割。手术那天,女孩吵着要见袁瑞,可她当时在另外的科室工作。妈妈告诉女孩,等你手术结束了,我们就和袁阿姨一起玩。可两个人还是没有见上最后一面。袁瑞在给孩子讲故事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一次次的分离,让他们渐渐学会面对工作中的爱与失去。有时候,他们也教着孩子如何与生命告别:有的志愿者给孩子们买了几条小鱼,可是鱼养不住,没几天就死了。孩子们吵着要和小鱼玩,社工告诉他们:「小鱼睡着了,它的生命到这一刻也就结束了。可是我们还是和小鱼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不是吗?」家庭:倾听与支持一旦遭遇疾病,受到冲击的往往不只是患者,还有他背后的整个家庭。患者家属往往面临着更大压力:紧张、担忧、无措的复杂情绪,日夜照顾的辛苦和疲惫,有时还包括难以解决的经济困难。这时,医务社工们选择成为「情绪出口」,给家属一个倾诉空间,让他们的负面情绪得以释放和缓解。袁瑞抱着孩子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袁瑞曾遇到过一个18岁的年轻母亲,她8个月大的宝宝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已经无法手术,只能听天由命。当时,身边所有的人都在指责她:哭有什么用,赶紧想一下解决办法。在医院的走廊里,这位年轻妈妈哭得快要抽搐过去,只有袁瑞走过去,抱着她:「心里很难受吧,没有关系的,那就哭一会儿吧。」孟燃面对的大多是肿瘤儿童的父母。得知孩子患上肿瘤后,家长们往往会经历一个「不相信、不接受」的阶段。除了向家长们传递科普知识,孟燃做的更多的是陪伴和倾听。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她曾遇到过一个家庭,父母都不识字,孩子查出淋巴瘤后,妈妈一直坐在角落里哭,孩子就坐在床上,紧紧捏着被子,不说一句话。狭小的病房里,越来越多的患儿家长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出主意。孟燃穿过人群,走到母亲旁边,轻轻拍着她的肩,倾听她的哭诉,陪着她冷静下来。因为只有冷静下来,才能面对疾病,解决问题。除了心理安慰,孟燃还帮着他们和医生沟通、带着他们办手续、联系病友提供帮助。当医生建议转院的时候,她又开始寻找这家人在当地的亲戚,联系家人的支持。社会:融入与改变其实,患病就像推倒了第一块诺米诺骨牌,随之而来的,是自信心、家庭关系、社会融入等一系列问题。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顾丽琪也是一名医务社工,主要服务乳腺癌患者。很多人告诉她,化疗结束回到家里,往往会更难受:和周围的朋友相比,总觉得自己不完整;在外面,还会受到各种异样的眼光。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是夫妻关系。有患者自己坚持治疗,可丈夫反对,觉得没有意义;有患者在电话里和丈夫大吵大闹,因为做了手术之后,丈夫再也没有碰过她;还有更激烈的冲突——手术同意书和离婚协议书同时摆在面前——「你要做手术,就离婚。」也有患者会干脆放弃:我做了手术,你可以出轨。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社会关系。顾丽琪曾有一位患者,化疗结束后回到家,恰好赶上朋友的喜酒。参加婚宴的时候,那桌的人已经坐满了,可是看到她坐下来,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选择离开。热闹喜庆的背景音里,她孤零零地坐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圆桌上,落下了泪。图片来源:站酷海洛创意作为社工,他们会安抚患者情绪,进行一些简单的干预:生病不是你们的错。但面对更多、更复杂的情况,如果患者不愿意沟通,他们也无能为力。孟燃也可以强烈感受到人们的「病耻感」——所有人都觉得得病是一件羞耻的、不光彩的事情,甚至患者家属,也会认为得病是自己遭受的「报应」。她曾遇到过一对父母,化疗结束后带着孩子回了农村老家。当地村民对癌症非常敏感,觉得他们家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才会生出一个得癌症的孩子,让上天来惩罚。亲戚朋友也渐渐疏远,有人直接跟自己的孩子说,他们家孩子得了怪病,会传染,离他们家人远一点。图片来源:站酷海洛创意面对这种社会偏见,医务社工需要通过他们的工作,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疾病,撕掉贴在患者身上的标签。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常常感到无力——如果说患者和家庭对于疾病的认知还可以通过干预来解决,但更大的群体对于疾病的偏见,太难撬动了。未来:收获与希望如今,社会对医务社工的认知度依然很低,他们工作中总会面临很多误解。有时候走进病房,还会被家属误认为是骗子、推销,甚至不会正眼相看,直接摆手说:「我们不需要,你们出去吧。」小朋友给孟燃「打针」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即使经常被无力感包围,医务社工们还是会感受到点点滴滴的改变。会被患者记住——医院里,会被来复查的患者突然喊出名字;也会有照顾过的孩子大老远地跑过来,突然抱住他们。医患关系也在改善——医院的某个科室工作一段时间后,那个科室的满意度总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当然,更重要的是患者在改变——化疗期因为呕吐反应强烈而拒绝进食的孩子,开始在她们的劝慰下吃下几口饭;先天唇腭裂的孩子,手里总是攥着一个手绢,遇到陌生人就会悄悄捂住嘴巴,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处,孩子终于敢放下手绢,接受周围的善意;严重烧伤的孩子,害怕回到学校,被人围观,在他们的陪伴和鼓励下,他终于能够坦然面对其他人的目光,回归正常的生活。医院向日葵社工站活动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医务社工和患者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患者的状态也会反过来影响社工,激励他们给予更多的